一
石板路旁,几株梅花,暗渡清香。
那是1929年早春,14岁的彭国涛一早起来,挑着一担茶水,跟随当教师的父亲,去迎接一支长途奔袭而来的队伍。父亲彭澎,明里是教师,暗里担任中共宁都县委军事部长。他告诉她:这支队伍叫红军,打仗非常厉害,其首领叫“猪毛(朱毛)”。
红军真的红眉绿眼?彭国涛有点害怕,她久闻红军青面獠牙,生食人肉。听说红军要来,国民党宁都县的县长赖世琮,亦望风而逃。
在县城南边十余里的石榴排,彭国涛见到了红军,却是些普通的人,有些失望。口干舌燥的红军队伍,似一条吸水的大龙,把满满两担茶水喝得精光。这支队伍被引进县城。当天,红军首领“朱毛”、陈毅等人,在城西温屋接见了他们。
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、闽西进军,处处受敌,疲于奔命,疲惫不堪。“朱毛”告诉彭澎:红军很需要银元、粮食,以及各种日用物品。
需要多少钱呢?
红军说了个数目:最好能筹集5000块大洋。
要这么多钱呀?
从没接触过钱的她,以为那是个天文数字。由此,她第一次学做群众工作,照样在父亲的带领下,向四邻八乡的老表们宣传共产党、红军闹革命的宗旨。没想到,竟然很快筹集到银元5500块、土布300匹、草鞋和袜子各7000双……
“ 朱毛”这名字响彻湘赣,其实是两个人,一个是军长朱德,一个是政治委员毛泽东。红军得到如愿的支援,军容大整,毛泽东说彭澎工作能力很强。接下来,发动群众,创办学习班,在县城上西门温家屋召开会议,成立工农兵革命委员会,毛泽东亲自任命彭澎为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主任,这是苏区宁都红色政权的第一任县长。
彭澎的“县长”,只执政十几天。5月上旬当选任命,5月中旬,红军离开宁都,彭澎便兼任宁都县游击队队长,带领县游击队转移到北部山区,开展游击战争。翌年7月,彭澎被捕。
彭国涛过早地介入革命,也过早地介入了痛苦。初阅人世,有两件事情系着两条命,令她刻骨铭心,永世难忘。
1929年初冬,骤冷的气温使人难以适应,彭国涛的弟弟彭寿平,突然不吃不喝,患了“哑口症”(白喉)。这在缺医少药的当时,就是大病。她与母亲陈氏苦守,巴望父亲归来。
那天,是12月8日。宁都县革命史上,一个著名的日子。彭澎与游击队副队长肖大鹏(后任红20军代理军长)等人带领游击队打进县城。当时,游击队有300多人,160多支枪,经周密布置,游击队一举捣毁县衙门,营救出关押在监狱的王俊的夫人及其他战友。
黑暗如墨的夜,三双眼睛似三对磷火,微弱地闪烁着,父亲一天一夜未归,弟弟的双眼,便在与妈妈、姐姐的对望中,永远闭上了。
彭澎回家,母亲抱着弟弟的尸体,泼命大哭,怨声不止。抚着独子尸体,彭澎愧疚不已,却并不悔错,哽声说:“这就是考验,我是共产党员,一切都是组织的,哪顾得了自己!”
考验,考验!面对生死,这两个字,彭国涛记了一辈子。
接下来的还是考验,更让她不忘记,那是眼见父亲绑赴刑场,壮烈牺牲。
游击战争,风餐露宿,彭澎积劳成疾,左腿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。战斗中时常发作,翌年7月的一天,队伍转战湛田乡李家坊,与大股敌人交火。彭澎行走不便,被敌人抓获,押送期间,却被会同区的群众抢救回来。
白军知其腿脚不便,行走不远,派兵轮番搜索一周,仍无结果。遂将会同区桐口、腰田、桃枝等村村民,集中于桐口村真君庙前,声言再不交出彭澎,烧毁全部房屋,枪毙所有村民……这时,彭澎突然从真君庙神座下挺身而出,大吼:“彭澎在这里!”
重新入狱,历经十几种酷刑,身残伤重的彭澎以死抗敌,他脱下身上唯一的毛衣,请送饭的牢卒换一包砒霜。毛衣是贵重物品,牢卒贪图毛衣,又惧怕死人,给他一包掺假的砒霜,彭服用后只落得个半死不活,被转押入县城大狱。
4个月毒刑。彭澎拒绝利诱,坚贞不屈。
为了儆戒民众,处决政治犯时,当政者喜欢搞公审大会。那年11月16日,一乘滑杆竹轿,抬着已经气息奄奄的彭澎,进入人群云集的县城体育场。
体育场北面司令台,台下,彭国涛用破衣遮头,隐在攒动的人群中,咬着嘴唇目睹父亲的惨死。
县清乡委员会主任邱伦才,站在台上,口沫飞溅,历数彭澎的革命“恶迹”,然后,煽动地大声吆喝:“大家说,象这样的坏人,要不要杀掉呀?”一些事先组织好的人,大声应答:“要杀掉!”混乱中,也有人喊:“不要杀掉!”
邱伦才又吆喝:“大家都说要杀掉,是不是?”
一位老者就说:“杀他做什么,他现在已经被打成毁人了,还是不要杀!”
询问大家,只是个形式,杀肯定要杀的。邱伦才命令刽子手用刑。
刽子手名叫刘炳南,得了36块银元杀人费。为了避邪,他穿一身白纺绸褂子,持一柄三尺长的鬼头大刀上了台。刘炳南是有名的刽子手,力气很大,但这次的活计却不利索,他挥刀猛砍,连续7刀,竟然没有把人杀死。
32岁的彭澎,脖子几处血水怒溅,射得旁人身上脸上,仍叽哩咕噜地叫喊: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
刽子手的手发软,有些慌,台下有人帮忙。嘶喊:“是他背上的标挡住了,要拔掉他背上的标,要拔标!”
刽子手慌里慌和拔标,再砍,第8刀就把头砍下来了。
“这,就是考验——”彭国涛昏倒在地。
白军把彭澎的尸体拖去喂狗,将他的头颅割下来,挂在城门上展览,7日后,头颅突然不见了,从此,尸骨无寻。
二
斩草除根,搜捕在继续进行,考验在顺序延伸。母亲被捕入狱, 15岁的彭国涛成为孤儿,四处漂零,躲藏到大山深处,过着野人般的生活。1931年,红军在荒无人迹的破庙里,找到了“野人”彭国涛。
中共宁都第一任县委书记,牵着这位烈士遗孤,在弹痕累累的红旗下宣誓。那年,她16岁,加入“共青团”,被派往父亲战斗过的会同区,就任会同区苏维埃妇女部长。她的工作范围涉及几十个村,十几里方圆。
动员和组织妇女拥军、支前、打草鞋、慰问红军、护理伤兵……踏着父亲的足迹,彭国涛积极性特别高,似有两条生命,风风火火地工作。很快,会同区苏维埃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,肉中刺。
1933年仲夏,一个月黑风高夜,乘苏区边缘空虚之际,白军的大刀会摸进区苏维埃,见人就杀。恶狠的大刀把门板剁烂之际,彭国涛翻身跳出围墙,仗着身子灵巧,逃得一条性命。慢她一脚的区苏维埃老文书,被剁成肉泥,命丧黄泉。
为了阻挡白军入侵,为了报仇,就要有强大的红军。
此后,扩红成为她最重要的工作。上级说:苏区能否生存、巩固,就在于红军的多寡。必须不断地扩红,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,苏维埃就胜利了。
彭国涛扩红扩了一百多人,她不知道一百万是多大的数目,只是走村串户,一家一户上门做工作,一个人一个人地动员。也许是因为没有扩大到一百万红军,红色政权没有胜利,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驮上马背,撤离了中央苏区,她扩红的一百多人也统统离开。
一走,就走得很远很远,一走就走了十几年。
白色恐怖四处弥漫,她又成为反革命追捕重点,似一条孤魂,在大山间飘泊,又过上了野人的生活。
时光在游荡中消失,每每生活苦到不堪忍受,人就会想到死,想到死时她就会想到“考验”,既然是考验,那就要活着,即使是为了考验。
敌人对她的追捕松懈下来,她的年龄也已长了上去。一般人家的女子,十六、七岁嫁人,她二十岁仍找不到婆家。因为,彭澎太出名了,彭澎的女儿也跟着出名,像麻疯病人一样。
在亲属的撮合下,四处流浪的她,嫁了个国民党33旅的大兵。姓黄,名叫黄国文,一个老实巴交的壮丁。
本想寻一棵小树荫庇,没料到,却是找到“蒺藜丛下躲雨”。
夫家原本家徒四壁,被她一“高攀”,虽无治罪,却受株连,立即销差,扒掉军服,取消俸禄,沦为苦力。
这对苦难夫妻,新婚期间便为生计所困,一个帮人挑水,一个帮人洗衣。这是最辛苦、廉价的劳动,一担水才卖一分钱,洗小孩的衣裳月薪4毛,洗大人的衣裳月薪5毛。即是如此,也没有多少衣裳来洗,他们得不停地揽活做。除了挑水,黄国文砍柴卖、帮人挑担、打猪印,彭国涛则帮人裁衣服、做扣子、帮人站柜台。
望眼欲穿。1949年7月,当年的红军终于回来了。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,她重新参加工作,担任了会同区南当乡妇女主任。在攻克翠微峰的系列战斗中,她积极支前,担任了负责检查、处理女俘的工作。由于工作出色,1950年,她调任梅江区(城关镇)妇女部长兼优抚主任,驻第四街街政府协助工作。她没日没夜,忘我工作,为红色政权的巩固、发展,风风火火地奔走。
1951年,作为革命烈士子弟的代表,她随南方老革命根据地代表团,邀请前往北京中南海,参加了在怀仁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,在天安门参加了国庆观礼,受到了毛泽东、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
在北京逗留期间,朱德听说老熟人彭澎的遗孤来了,还特别发出邀请,她应邀来到朱德总司令家里作客,叙述了自己的生命之路。数十年后,朱德的女儿朱敏,重访老区宁都,还特意找到她长聊。
革命在不断升温,不断升温的“革命”十分讲究颜色,她越来越红,他便显得越来越白。
女人的荣耀,就是男人的灾难。黄国文,成为家庭中一个尴尬角色。国民党大兵的历史,使他如履薄冰,颤颤惊惊。
1951年早春,几匹来自北方的大洋马,急促的脚步把鹅卵石巷道击得直冒火星同,马群嘶叫,直奔米市巷--彭国涛家。
“砰砰砰--”门被敲得很响。黄国文从门缝瞧见,大洋马后面,威风凛凛,有3个身着军装,荷枪实弹的人。他被吓坏了,估摸这伙解放军是来捉自己的,想溜,腿脚抖得像筛糠,拼命使劲就是迈不开步子。
来者,是解放军某部的刘师长,衣锦还乡。当年,是她爬山涉水,去那个人迹罕至的山村,从牛背上把他拽下来,扩了他的红。他把手中的竹鞭一扔,拖着两条大鼻涕,两脚泥水,走上一条光辉的战斗之路。饮水思源,刘师长不忘自己革命的引路人,特意来寻源谢恩。破屋里,看到还很没有“进步”的恩人彭国涛,刘师长带她去走访了专署专员,县委书记、县长。
临别,刘师长悄悄地但却明确地劝她离婚:“一个红军干部,烈士子弟,与一个白军搅在一块,会冲淡颜色哩!”
县里也有意,要让她担任县委妇联主任,可是,她还不是党员,红光灼灼的县委妇联主任,背后立着个白军大兵,那政治影响肯定不好。
蕴意婉转而明确,何去何从?
这是一个政治难题,也是一个人生考验呀。结婚之日起,木纳的老公就在思想、经济、生活上,日愈处于从属地位,连她生育的儿女也统统随母姓彭。解放后,他成为一名菜农,与她的干部身份拉大了距离。迟钝的丈夫,也屡屡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别扭,多次提出:会妨碍她的前途,就……
在仕途与良心的考验之间,她踌躇许久,最终战胜诱惑选择了后者。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一个善良者,出于一种善良的本能,她不能伤害无辜,伤害相依为命10几年的老实人。
这,肯定是政治思想觉悟不高,阶级立场不稳,没有经受住考验。
她的入党延期了。既不是党员,那也不适于长期待在区委。1958年大跃进,城关镇让她到街道去筹建缝纫社。这也许算是一种贬职,对此,她把帐算在丈夫身上,理解得很天真:过去,自己株连过他,他在白军中被销差;现在,他株连自己,自己被红色区委贬职,一销一贬,算是扯平了。继续经受考验吧!
初时,缝纫社10几个家庭妇女,3、4台缝纫机。经一年努力,业务不断扩大,发展为有6个门市部,近百名职工,月薪从10几元提高到30多元。
哪里艰苦到哪里去,1959年,县里要在一片荒山坡组建光荣敬老院,又派她去负责。那是一桩更艰难的工作,而她的工资则相反,不但不升,反而降为收入20多元。她很为难、犹豫不决,那时,她坚持不懈积极要求入党,党组织说:去吧,要经受得住考验。
她去了那片荒地,经受组织的考验,更是经受人生的考验,却仍被挡在党的大门外,永远面对并承受--这片遍布疮痍的土地和现实。
大校场,在当地也读大“窖”场,“窖”是葬的意思。大校场,古代的演武之地,演武时演死的人,就地埋葬,早已落魄为一片荒山野岭,人高的荆棘丛中,时而冒出几座坟墓,随处可见森森白骨。
老枯树、荒草,地洞中出没着蛤蟆、野兔、大极了的蚱蜢、油葫芦、蟋蟀。有一只鲜艳如火的红狐狸,常常从眼前一掠而过,熟悉了,它有时会突然出现在屋门口与她对视。
过过野人生活的彭国涛,并不惧怕大自然的荒凉,她喜欢那只火狐狸。
选择地址、设计绘图、选料、请工、监理、参加义务劳动……一应事宜,无不艰辛,由她全程料理。一切从头干,从头学。遇到太困难、伤心的事,她流着泪想:再困难也要挺住,要干,这是党在考验我呢!
半年后,第一幢住宅拔地而起。几经动员,烈属们却不愿意去住,认为:光荣敬老院只是嘴巴上光荣,生活艰苦,一伙鳏寡孤独凑在一起不体面。她第一个便把老母亲接进院,她的母亲是一个座标,是全县举足轻重的烈属代表。接着,她动员第4街烈属第一批入院,然后把城关镇一街一街的烈属,及全县的烈属老人接入院内。
数十位老人的护理,吃喝拉撒,衣医住行,无异于一堆堆难缠的乱麻。那年,她42岁,担任宁都县光荣敬老院院长。从此,她深陷其中数十年,不能自拔。
三
以40余岁的健壮年华,徐徐注入鳏寡老人们衰朽的躯干,彭国涛迎得了信赖。
松风飒飒,蒿草森森,日睹狐兔出没,夜见磷火闪烁。属兔的彭国涛,不畏凶狠残忍的仇敌,长的却是兔子胆。然而,她又怕不了,走马上任,出师不利,第一个星期,有两位老人接踵去世。
为避邪,院里的人大部分躲离了。院里无男丁,彭国涛就自己动手,按地方风俗买水为死者擦洗净身,与院里唯一的女服务员,抱头扛脚,装殓入棺。死人入殓,要在灵堂里停放7个7,7个7,49个夜晚都要有人守夜。别人不守,彭国涛就自己来守。
山荒夜寂,风声鹤唳,鬼哭狼嚎,无不骇人。为了壮胆,夜里不敢熄灯,山风过坡,呼--一声,灯火像似鬼火摇晃,屋子里一阵乱响,火“卟”地灭了。那一只火红的狐狸,会跑到屋里来与她作伴,把她们吓得半死。保险起见,她们便点燃两盏灯火,却又心痛油钱。为了省油,后来,她干脆要求丈夫每晚收工后,赶到敬老院来陪住。
死人难守,活人更难护。逢风雨之夜,行动不便的老人起夜,她也得起夜。数月下来,她面黄饥瘦,脸庞小了一圈。再这样拼下去,命都会拼掉。家人劝她别干了,一月25元收入,值吗?她置之不理,说,再困难也要挺住,要干,这是党在考验我呢!考验,你们知道吗!
非共产党员彭国涛,记住父亲是这个县共产党的创始人,她处处照父亲的样子去做,也就是共产党员了。
40多个烈属,7老8十,个个都是烈士的父母,现在只能靠自己来做孝子。他们都是自己的父母一般。精心照料着入院老人们的生活,人病了,她当护士;人死了,她当孝女;老人事多,这个不病那个病,她常常中夜而起,为老人到水、喂药、掖被子、端便盆;白天则缝补浆洗采买物品,忙碌不停。
她日夜奔波,为敬老院接进了水、电;建起了院墙,喂猪养禽,种植了4亩柑桔树,数十株板栗;开垦了3亩蔬菜地,每年可达几千元收。她收留三个孤儿,一个成了国家干部,两个成了敬老院的强劳力。
敬老院的条件日益改善,生活越来越好。老人们由不习惯到习惯,继而把敬老院当成了自己的归属,自己的家。有几位老人,还认彭国涛作契女,把她当成亲生女儿。她则把院里的老人都当作父母。可是,一人服侍40多个父母,父母是不是太多了!
40多个父母确实太多了,但他们都是烈士的妻子、父母,他们倚门倚闾,烈士在九泉之下会不安的。想到烈士,彭国涛不嫌多,始终不厌其烦,一如既往地侍候老人们。
90多岁的老人陈门女,瘫痪在床,大小便失禁。一日两次,彭国涛用热水为其擦拭身子换衣服,直到半年后病故。
卢方才老人神经失常,是个文疯子,生活不能自理,且时有惧人之举,人们都离他远远地,只有彭国涛一人服侍、调教他煎药、喂药、喂饭、喂水、抓屎抓尿。另3位年岁太高的老人,行动不便,诸如洗衣服、晒被子、生火笼暖脚,所有的杂事也都得彭国涛亲自料理。
开荒种菜,栽种果树,养猪喂鸡,天气暖和的日子,她会带一些健康的老人去拔草,收获果子……院里的生活逐渐得以改善。
渐渐地,彭国涛成了老人们的手、脚,成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。老人们信任她、爱戴她,离不了她。
有一年,县里筹建按摩诊所,调她去担任所长。只两天时间,老人们怅然若失,惶惶不可终日。几十名颤颤栗栗的老人进城集体上访,流着泪水坐到了民政局里,不吃不喝不讲道理,硬是要上面把“彭澎的女”调回来。老人们的子女的名字,就是该事的革命历史,这个事件惊动了县城,人们突然想起,原来世上还有这样几十名颤颤栗栗的老人,想起了“彭澎的女儿”,想起了彭澎。
彭国涛的婚姻,既是在“蒺藜丛下躲雨”,没有躲过雨是另一回事,却必然要挨刺。
历史问题不但会历史下去,而且会变得现实起来,成为现实问题。“文革”时期,丈夫的白军大兵身份又一回大大张扬,她全家再次受株连,下放到偏远的琳池乡。一年后,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,陈昌奉担任了省革命委员会主任,回家乡来看她。询问她的情况后,说:“你是老革命,烈士的后代,应该彻底落实政策。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。”
从乡下赶回来,她被接见,只提了一个要求:恢复工作。
在省领导面前,县领导也慷慨大方得很,赶紧说:提吧,县革委会正缺人,到哪个部门都行。你是老革命,工资、待遇补发补办都应该。
那场“文化大革命”,可以对以往的历史失误进行修正,也可以对以往的革命进行革命。
她开口了,却要求回光荣敬老院,说:“那儿,还有几十个烈士的父母,没人关照,吃喝拉撒都成问题,生老病死都没人管!”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下放的数百个日日夜夜,几十位烈士的父母,萦绕心间,成为她心灵的创伤和恐惧,以及丧失家园的那种致命的孤独和隔绝。她的眼睛和神情,涌流出一种人性的震憾力:炮打火烧的“文革”硝烟中,她必须去引渡老人的灵魂。
光荣敬老院--那是她的全部世界,她要为革命老人做一代孝女。
对于敬老院,“文革”中多有微词:光荣敬老院--嘴巴上的光荣;院长--实际上是老保姆。听了她的选择,陈主任与县革委领导对视,欲言又止,只得随她去了。
时间的风霜,无比凌厉,在彭国涛额头上镌刻下深深的皱纹,她老了。近十年来,她不仅担负着敬老院里繁重的工作,还兼职当人民陪审员、县人大常委、县政协常委,从事大量义务的社会活动。
多年来,她以忘我的工作为“彭澎的女”,赢得了一串串荣誉。她曾三次上北京,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;多次受到华东军区陈毅司令、民政部、天津、南京市人民政府、江西省人民政府宴请;曾数十次荣获全国、省、地、县“双拥”先进个人奖、“老有所为精英”奖等。
闲下来时或梦中醒来,她会突然想到那只鲜艳如火的狐狸,它到哪里去了,怎么不来看我呢?!
敬老院里,她上上下下忙碌着,随时是和颜悦色的,带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。这种笑容,只有与世无争,生活上感到满足的人才会有。
但她并不满足,她的入党要求没有批准。她认为这个党是她爸爸的,她一定要加入,年年都递一份申请书。
她感到苦恼的是:年复一年写申请,考验了40多年,怎么党就不批准自己?
四
1985年,老枝萌芽的季节。
彭国涛往来于县委党校的路上,荣幸地参加了县直属党委举办的党训班。上百名青年男女间,突兀着一个白发皓首的老人。青年们从小听她讲传统长大,以为这位老奶奶是来讲党课。令人吃惊:这个响当当的先进,三次进北京参加国庆观礼,数次到省里参加“双拥”先代会,年年上报、广播表彰的人物,竟是党外人士?
彭国涛也十分吃惊:过去自己要求入党时,没有一个人要求入党。现在,要求入党者竟然成群结队。
不知是第多少次进建党对象培训班,结果仍是“陪训”。每一次培训,几乎所有的受训者都入了党,唯她例外。问其原因,谁也不知道,成了一迷。
她说:“组织上一直在考验我,50年了。”
1987年7月,当年曾劝她离婚的刘师长回乡,在县委大院,大发其火:“彭澎的女不是共产党员,谁还配?”
--两个月后,她成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。此年,彭国涛72岁,申请入党52年,被考验52年。从“共青团”到中国共产党,这一步,竟跨越了半个多世纪!入党不久,她就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。
也许,她早就是一名优秀党员。她“早就是”的东西很多,却不是。是――不是,之间真有那么遥远么。
遥远而又现实。4、5个孙子孙女,全体待业,烽烟四起,免不了冷嘲热讽“围攻”她:你是1929的“老革命”,到现在,为什么还不是国家干部?外祖父活到现在,少不了是中央级干部,他为国捐躯,为什么,我们满门忠烈,连一个国家编制的工人都当不上?有人“新革命”,当了点小官,老婆子女安排得风风光光?你死要面子,为什么不帮我们说说话?!
对这些时代的毛病,彭国涛很隔膜,常常无言以对,于是,她就想起了“考验”,猛然冲出一句话:“你外祖父命都去了,尸骨不留,我们又贪什么呢!”
有时,她也奇怪:国家干部60岁“一刀切”,自己70多岁的临时工,怎么还退不下来。敬老院长,虽是不起眼的小官,毕竟是国家这“大组织”的一环,她不想搞特殊化,可是,不想特殊的她,却推辞不了那特殊的职务。
考验、考验,难道这一切都是考验吗?!
那年,日愈苍老的彭国涛,做了胃切除手术,医药费、营养费、生活费……没有出处。有关领导,接待了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上访,但不知如何解答这个老人关于“革命干部”和“国家干部”的含义。事实是,尽管她1929年就掖着脑袋“闹红”,至今,只是个每月拿60元优抚金,加上临时工月薪25元等,总收入100多元的优抚对象。当年,她扩红百余青壮年参加红军,有的人成为将军和省市级领导,她却仍是担任宁都县光荣敬老院院长的临时工。
一条布满荆棘充满艰辛的人生之路,她已经执著地走了80多个春秋,迈着龙钟步履,她仍然走得那么从容,走得那么坚毅。
彭国涛是睁着眼睛死的。死前一日,考验终生,久病迷糊多年的她,突然清醒异常,竟像个初世孩子望着面前这个久违而陌生的世界,声音软软地说了一席很“天真”的话。
“我今年86岁,有两件事情想不通:一、父亲为革命割了头,革命成功50多年了,他的头没找回来,连座坟茔也没有;二、自己革命70多年,并非临时革命者,连临时的念头都没有过,还是个永远的临时工。”
彭国涛有个外孙名叫赖国芳,是县政协副主席,他将此言告诉笔者。
我楞楞地想了许久,心情异样沉重:大众传媒、公众目光,有意无意忽略了那苦难历史。这种忽略,是一种群体忘本,比事情本身更加残酷。
彭国涛留给这个世界的话语,柔柔的,却突兀、尖锐。她终生都在经受这个社会的考验,也用一生来考验这个社会。既是考验,总该有个结论吧。这个社会对她的结论,她对这个社会的结论会是怎样呢?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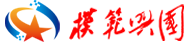



请输入验证码